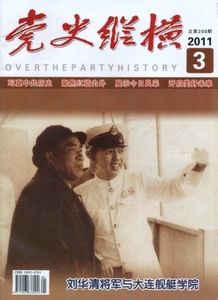
本文摘自《党史纵横》2011年第03期,作者:魏德平,原题:《习仲勋与“陕北肃反”》。
1935年9月下旬到10月中旬,西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两部分,发生了严重的“左”倾错误肃反。中共北方代表和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通过不同的途径得到西北革命根据地“问题严重”的报告,遂派遣朱理治、聂洪钧等人赴西北解决问题,加强领导。1935年,朱理治、聂洪钧先后抵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后,结合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某些地方领导人,依靠刚刚开赴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红25军,秉承上级有关肃反的决议,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一场主要针对陕甘边根据地和红26军党政军领导的肃反运动。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陕甘根据地的开创者,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者被逮捕,并遭到残酷的刑讯折磨,“凡是原红26军营以上的干部和西北军委机关、陕甘边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以上的干部几乎全部被捕”,其中230多人被杀害。这次肃反造成了当时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并使西北根据地老干部间发生了长期的争论。时任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也受到酷刑的刑讯折磨和“莫须有”的政治污蔑,甚至生命威胁。正如他自己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痛心地说:“毛主席不到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说‘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指‘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那么这场残酷的内部肃反是怎么发生的?习仲勋在这场生死攸关的错误肃反中又经历了怎样的磨难?
西北革命根据地内部的历史积怨及其对陕北肃反的影响
陕北肃反之所以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出现,革命者内部自相残杀,且手段极其残忍、后果贻害无穷,都与西北革命根据地内部的分歧长期得不到解决,且逐渐激化有密切关系。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比较复杂的,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是从各自独立战斗,后来慢慢走向联合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曾担任陕北红军27军81师师长的贺晋年说:“1935年前,陕甘边和陕北是被敌人分割开的两块根据地、两支革命武装,因而也就存在两个领导关系。陕甘边根据地和武装属于陕西省委领导;陕北根据地和武装则受中央驻北方代表的领导。在革命斗争中,两支革命武装虽然常有联系和配合,但基本上是各自进行活动的。”陕甘边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曾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的张秀山也说:“1934年7月,谢子长、郭洪涛带领陕北游击队来到南梁,老战友相见非常亲切。……在此之前,陕甘边特委与陕北特委有些联系,但是因受敌人包围和阻隔,往来不多。两个特委又分别属于两个上级机构领导,陕甘边特委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陕西省委归党中央直接领导;而陕北特委归中共北方局,其后为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双方逐步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和互相支援,最后在刘志丹、谢子长同志的领导下,于1935年2月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了完全统一。”
但是,西北党和红军在发展中也产生了很多分歧,留下了一系列难以抹平的矛盾。1932年1月发生的“三甲塬缴枪事件”就是突出的一例。“‘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武装全国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指示,将南梁游击队改称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朱李恺任参谋长,师储杰任第一支队队长,杨仲远任参谋长。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到西安附近活动,以扩大影响,刘志丹不同意,他主张在陕甘边活动。在这期间,部队进行整顿。有人主张整顿要缴械,刘志丹主张整顿要加强教育,贫苦农民出身当过几天土匪的要改造,也能够改造。但是,没有经过西北反帝同盟主要领导成员的讨论,没有请示省委,就委任执法队长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制造了‘三甲塬收枪’事件。执法队打死了刘志丹带领的二支队的一个骨干,收了二支队的枪,也缴了刘志丹的枪。根本没有革命准备的师储杰获悉发生此事,极为恐惧,带领部队投敌。一支七八百人的队伍,转瞬间只剩下100多人。”策划和主持这次缴枪行动的人是谢子长,阎红彦是杀死刘志丹二支队骨干赵二娃的执法队队长。刘志丹当时被缴械软禁,直到第三天陕西省委巡视员到来后才被释放。为此,当年3月下旬,刘志丹还亲自到西安找到陕西省委申诉,陕西省委去信批评了谢子长和阎红彦。
1933年5月,红26军南下创建渭华根据地失败后,西北根据地主要领导在追究失败责任时,又发生分歧,加大了矛盾。在“三甲塬缴枪事件”以后的大约两年时间内,西北革命根据地在曲折中逐渐得到了发展,尤其是陕甘边发展尤其迅速。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与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刘志丹等的探索是不开的,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刘志丹慢慢找到了革命的正确道路,取得了许多辉煌的业绩。1932年7月,刘志丹对当时搞“两党(地名,在今甘肃东部)兵变”失败的习仲勋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1934年5月28日,陕北特委也得到恢复。陕甘红军队伍,不久也从创建渭华根据地失败的阴影中冲了出来,恢复了红26军42师,到1934年10月“红42师已拥有五个团的建制,其中包括郭宝珊率领的抗日义勇军,兵力近千人,游击队发展到1500余人。”
但是,在此期间,西北革命根据地内部“左”倾错误也在恶性膨胀。当时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边,推行“左”倾路线就是典型的例子。杜衡来到陕甘边后即改组红26军,自任军政委,火烧始建于唐代的照金著名庙宇香山寺,进攻与陕甘边有统战关系的地方武装,不切实际地提出建立新的渭华根据地。在1933年5月,在杜衡的强迫和煽动下,刘志丹只能率领当时组建不久的红26军2团开往渭南、华县一带创建新的根据地,在开赴新根据地的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伤亡累累。此时的杜衡畏惧困难,以回西安汇报工作为名离开这支队伍,不久在西安被国民党逮捕,随即投敌叛变。刘志丹率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队伍也被冲散,刘志丹藏身终南山,后在当地党组织帮助下,历尽千辛万苦才辗转返回陕甘边根据地与留在那里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等汇合,继续开展革命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
红26军南下创建新的根据地失败了,而且大伤元气,那么为什么会失败?谁应该对失败负责呢?毫无疑问,杜衡及其推行的左倾军事路线,不顾红军实际情况,盲目行动是造成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而且杜衡的叛变更加重了红26军的损失。但是到了1934年前后随着谢子长、郭洪涛先后回到西北革命根据地后,对失败的原因和责任有了新的“解释”。1934年7月2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42师委员会,在南梁堡附近的阎家洼子召开了连以上的干部会议,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传达北方代表的指示,并邀请中共陕北特委委员郭洪涛和陕北红军游击队各支队领导干部参加会议。“谢子长在会上宣读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26军的两封信。信中对红26军的战略转移指责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西北地区人民对山区的称呼)主义’、‘枪杆子万能’,说部队组成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郭洪涛在会上也作了严厉批评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的发言。
“郭洪涛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从国际讲到国内,从无产阶级发展讲到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又讲到陕甘边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红26军不能正确执行党的路线,重复了北方代表指示信中那‘五顶大帽子’。”随后,郭洪涛在陕北特委的机关报上发表《红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照抄照套上海临时中央和北方代表给红26军的两封信,批评指责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1934年8月26日,谢子长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负了重伤。9月5日,谢子长在病榻上给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写信,对红26军42师及其领导人刘志丹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42师一贯的是军事乱窜,不能在艰苦的群众工作中完成西北苏区的任务。渭北与照金的失败,红26军不能扩大,都是政委不能把握中央路线的缘故。虽然联席会议暂时要我代理42师政委,但是我在军事上较有把握,在政治上非常困难。联席会议一致的要求中央派军、政同志领导42师,把老右倾同志另外调换工作,才是根本转变26军的办法。”“联席会一致的认为,领导关中、陕甘边、陕北、甘宁等的实际工作里,需要中央派得力同志去组织西北代表团,或组织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西北全部工作。”稍后,10月26日,陕北特委郭洪涛也致信“中代”(这里指的是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他在此时负责领导北方中共党的工作),指责红26军是机会主义、梢山主义、逃跑主义等,同时要求“中央派代表驻西北,统一领导西北工作。”
谢子长、郭洪涛给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信,导致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以及主管中共白区工作的上海临时中央对陕甘边根据地的不信任。同时,按照谢子长、郭洪涛的请求,中共驻北方代表孔原、上海临时中央局分别派出了朱理治和聂洪钧,奔赴西北根据地加强领导。由于这样的缘故,不管是朱理治还是聂洪钧,在抵达西北根据地前就都已经对陕甘边和红26军主要领导成员有了偏见,带着“改造”、“整肃”红26军和陕甘边根据地任务而来。
当时陕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时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长)的郭洪涛给朱理治、聂洪钧等反映的关于陕甘边和红26军的大量负面材料对肃反的发生产生了极大的诱发作用。郭洪涛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及自己在陕北肃反中的责任时说:“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来到陕北后,我向他讲过我误信别人反映的陕甘边特委一些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情况和错误意见。……造成了对红26军老干部的不信任。”当1935年7月5日朱理治抵达西北根据地后,“郭洪涛向朱理治介绍了西北苏区的历史和现状,在介绍主要负责干部时,既说到他们的长处,也说了他们的短处。在介绍陕甘边和红26军的干部以及部分陕北干部时,较多地介绍了他们的‘短处’:刘志丹家是地主,父亲是民团团总,他一贯的右倾,是白军军官,带来了不少白军的影响;1933年红26军搞垮,不仅是杜衡的错误,也是刘志丹的责任;刘志丹、高岗恢复红26军以后的路线是错误的;他们是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富农路线;高岗政治上弱,没有能力,文化程度低,最调皮捣蛋,开过小差;马明方(陕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时任陕北特委宣传部长)执行富农路线;张秀山、习仲勋是老好人,没有什么能力;贺晋年是军事冒险家、英雄主义;马文瑞被派到三边去,一年多没有回来,没有写过信或写过报告;高朗亭贪污了八十块钱;西安来的都不可靠;张文华、李西萍都是右派,都是通过红26军和西安的关系来的等等。”“因为‘中代’(这里指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要求朱理治到西北后要信赖郭洪涛,解决陕甘边和红26军‘右倾’问题,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因为郭洪涛的介绍与上级的交代在总体上一致,加上他是陕北人,长期在陕北工作,朱理治相信了他的介绍。朱理治没有与被认为有问题的陕甘边和红26军负责人谈话了解情况。”1935年9月1日,上海临时中央派遣的聂洪钧抵达西北根据地永坪镇后,聂洪钧也听到了基本相同的说法:“在西北工委半个多月时间,从郭洪涛、朱理治同志的口中,几乎随时都可以听到这样的一些谗言和说法。”由于这些原因在朱理治、聂洪钧一抵达西北根据地就对陕甘边和红26军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这就是日后肃反展开的时候,主持肃反的领导核心一致推行肃反的思想政治根源。
红25军抵达陕北后,西北革命根据地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
朱理治、聂洪钧先后到达西北根据地后,由于不了解当地实情与原主持西北根据地党政军工作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加深了朱理治等人对陕甘边和红26军主要领导的“成见”。
1935年“七月中旬,朱理治在文安驿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讲了两三天。从国际讲到国内,从中央苏区的伟大胜利(实际这时中央苏区已经丢失了)讲到陕甘,当着我们的面(这里指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主要领导),说我们在政治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是‘枪杆子万能’等等。在讲到陕甘苏区当前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时,提出要‘全线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土地’,要红军配合‘地方暴动,消灭在苏区内敌人的支撑点(即敌人重点固守的城镇)’,要红军‘去打延安、清涧和瓦窑堡’等城市,‘开展敌人侧翼及后方的广大革命战争的战线’,‘运用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粉碎敌人的新‘围剿’。还提出,‘争取神府和吴、绥、川南苏区打成一片,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韩城发展,恢复失去的米东、庆北、华池苏区,开展洛川工作,消灭甘、等地的白区,以洛川为中心,积极向定边、陇东发展,以马栏为中心向潼关、富平、泾阳发展,坚决巩固向南发展的路线’。”朱理治提出的这个明显带有“左倾”的而且连地理位置都没有搞清楚的战略方案遭到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的反对,“会上,不少同志你一言我一语,使他们(指朱理治、聂洪钧等)很下不来台”。“会后,刘志丹等同志没有执行打延安、瓦窑堡、清涧的攻坚计划,仍按西北军委原定的作战计划,向北线敌人出击。”这些分歧加深了朱理治等对刘志丹的“固有成见”,在随后由他主持召开的“西北工委扩大会议”时,没有让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成员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张达志等参加,并且秘密通过了要在陕甘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肃反的决议。这其实已经将肃反的目标开始确定在了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上了。